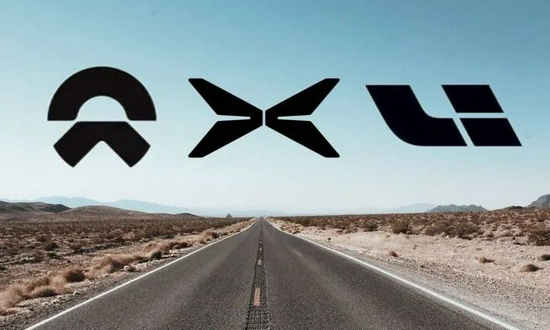一家日本新造車 決定去美國IPO了
挺禿然的。
日經新聞剛剛爆料,日本一家電動車初創公司HW Electro,即將去美國納斯達克申請IPO。
和中國、美國的新能源汽車的環境相比,日本對于電動車的態度一直都是模棱兩可。豐田作為帶頭大哥,也給出了明確態度——不看好電動車的發展。
豐田、本田這種巨頭轉身向來困難,但并不意味著日本電車沒有生存環境。
HW Electro就懂得錯峰競爭,把目光聚焦在了小型商用電動車市場。而且追溯這家日本新造車的發展歷史,這背后竟然有很多中國人。
中國制造的“反向輸出”
雖然是一家日本車企,但從創始人到平臺技術,處處都透露出了“中國造”的影子。
這家名為HW Electro的企業,是一家主要研發輕型商用卡車的初創公司,成立于2019年,2021年4月,成為日本首家獲得牌照號的進口小型EV商用車的企業。
最開始在2019年1月舉辦的東京汽車沙龍上,在一家名為Good ride輪胎制造商的展臺上亮相了自己的首款原型車型——Elemo。
有意思的是,當時只是亮相,并沒有在日本開賣的計劃,只是單純地展示了自己的車使用了Good ride的一款輪胎。
而Good ride輪胎的中文名是好運輪胎,總部位于杭州,是國內制造業500強,參展時在世界輪胎制造商排名中名列第8位,還是國內最大輪胎生產企業中策橡膠的旗下子品牌,旗下還有一個家喻戶曉的品牌——朝陽輪胎。
HW Electro的創始人,就是彼時任好運輪胎日本區總裁的蕭偉成。
蕭偉成出生于中國臺灣省,2歲時就跟隨家人到了日本,最終定居在日本。擔任好運輪胎日本區的總裁時,還組建了一支Good ride的賽車隊。
決定蕭偉成創立電車公司的契機,是2018年一次大阪北部地震中的停電,雖然只是幾個小時,但其表示,在停電的街頭徘徊時,手機電池耗盡,感到非常不安,也認識到了電動汽車的重要性。
正是因為這個想法,蕭偉成創立了HW Electro。
剛剛成立時,日本的小型商用電動汽車只有三菱的“minicave meve”,另外還有從海外引進的DHL子公司的輕型卡車,所以當時確實是有市場。
但白手起家的蕭偉成,沒有足夠的資金布局上下游,為了控制資金,他想到了引進平臺化車型再加以改造進行銷售的想法。
2019年的東京汽車沙龍現場,展出的HW Electro的原型車輛 Elemo,就是基于美國公司CENNTRO的電動汽車平臺打造的Metro。
這家位于美國的CENNTRO公司就有意思了,是一家專門研發平臺化車型,然后開發符合各國需求電車的公司。例如,美國電動汽車制造商ARYO,就是利用這個平臺開發了移動疫苗接種車輛。
CENNTRO公司雖然總部在美國,但還有個中文名稱,叫恒源電動汽車集團,于2013年由王祖光和數名互聯網行業人物聯合創立。
沒錯,也是中國人。
王祖光算是是科技界的連續創業者,畢業于美國伊利諾伊州大學,取得計算機電氣工程雙碩士學位, 最被公眾熟知的頭銜莫過于“小靈通之父”和“中國首家納斯達克上市企業締造者”。
90年代回國后和薛蠻子、陸弘亮一起成立了Unitech Telecom (UT斯達康),2000年3月,UT斯達康成為中國第一批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之一,成功地推出了光環路系統和無線環路系統。
而恒源集團的核心團隊,曾擔任國內外企業高管職位, 其中包括了谷歌中國、美林銀行、沃爾沃集團等,公司天使投資人包括李開復、薛蠻子、徐小平等一眾科技大佬。
HW Electro的原型車邁圖Metro,就是基于恒源電動汽車集團的“容大智造”平臺生產出來的。
這個平臺整合了電動汽車的研發、設計、生產、供應商、金融服務、維修保養等領域的服務商,以幫助新造車公司實現輕資產造車。
這臺車在汽車沙龍展出的時候甚至還使用了邁圖的中文名,引進日本后,才被HW Electro換了自己的名。
換句話說,就是拿中國造好的車,稍微整改一下,再放到日本市場去賣,當然,引入日本的過程也是下了點“功夫”的。
對于日本市場而言,國外生產的商用車往往無法承受日本嚴酷的氣象環境(高溫多濕,積雪地區也多)和城市擁堵等高強度的使用狀況,為了在日本得到認可,需要調查每一個零件是否達到標準。
當然了,HW Electro還需要改變一些零件,以適應日本的駕駛環境,比如優化腿部空間,并增加了100V/ 1500W插座和踏板誤用預防系統。
2021年4月,HW Electro 成為日本首款獲得牌照號的進口小型EV商用車的企業,自此HW Electro的第一款車型“Elemo”正式進入市場。
綜上來看,HW Electro其實并沒有太多核心技術。
日本新造車還得靠中國人?
在日本,HW Electro的經營模式并不是個例。
成立于2021年的日本電動車初創企業Folofly,發展路徑和HW Electro相同,不過Folofly更加徹底。
Folofly的創始人小間裕康(Hiroyasu Koma),最初是瞄向了純電跑車業務,但后來跑車業務虧損太大,入不敷出的情況下開始調整業務方向,最終選定小型商用車市場。
不過日本對于拿車牌照的要求很高,需要通過上百個零部件檢測項目,才能達到日本國土交通省規定的安全標準,這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力。
怎么才能最大程度節省資金?
“有好辦法,(就是)利用中國的力量。”小間裕康此前曾和中國車企有業務往來,Folofly也就順勢走個捷徑——找中國車企代工,用中國廠商的檢測數據可以大大減少生產和運營成本。
其首款車型,就是由中國東風汽車集團旗下的東風小康汽車代工生產。
而Folofly引進的商用電車,主要是用于在“最后一公里”物流配送,是和日本物流巨頭SBS控股簽訂合同。該車型車型負重達到1噸,標準續航300公里,更重要的是每輛車的進口成本只要380萬日元(折合19.2萬元人民幣),與油車成本相當。
Folofly表示,目前這款合作電動貨車基于中國市場上在售的油車改造而來,增加了防抱死等系統,但整體來說改動不大。據Folofly當時介紹,在中國生產能夠把每輛車的售價控制在400萬日元以下,同樣的車在日本研發并生產,標價至少要1000萬日元。
去年6月,Folofly推出了該公司設計的第二款小型商用純電動卡車,同樣由東風小康汽車生產,價格約在380萬日元左右(約合人民幣18萬元)。
在此之前,日本企業曾為在中國市場銷售汽車而向當地企業提供技術。但是在電動汽車新產業規則下,這一格局徹底扭轉。
其實說起來,早先的日本電動車市場并不像現在這么拉胯。
七十多年前,日產就推出了第一款電動車TAMA,1983年,日產推出世界首輛交流異步電動機電動汽車——日產MarchEV,到了2010年,世界上第一臺量產搭載永磁同步電機的電動車LEAF聆風發售。
日產Leaf也一度成為全球最暢銷的電動車,連續8年獲得全球銷冠。
但隨著特斯拉Model 3的到來,作為日本電車的招牌,日產Leaf逐漸掉隊了。再有最近幾年全球汽車行業風云突變,自主新能源車企“一超多強”的格局逐漸形成,除了一馬當先的比亞迪外,吉利、廣汽等傳統車企也開始孵化新生品牌,實力和地位早已和十年前不同。
如今中國新能源汽車品牌正拼盡全力搶下一輪門票,城市NOA、激光雷達、芯片算力等領域競爭尤為激烈,反觀日系車企則是踟躕不決,時不時還放出驚天言論,反擊目前電動化的成就。
前不久,索尼本田移動出行公司(Sony Honda Mobility)的社長川西泉就放出狂言,稱中國電動車沒有技術驚喜,就像是把智能手機的圖標拼湊在一起。
和HW Electro、Folofly不同,索尼本田移動出行公司是地地道道的日本新勢力造車,由索尼和本田共同打造,可以說是日本新造車的獨苗。
但其首款車型“AFEELA”的原型車,在今年10月才剛剛亮相,2026年才能量產開售。
現在國內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競爭局勢,幾乎是按天算的,稍不注意就會被甩在身后,誰也不知道,3年后索尼電動車會遇到怎樣的對手。
不過無論索尼本田交出一臺什么樣的車,可以確定的是,當川西泉開始炮轟中國電動車時,中國電車就已經贏了。
本站所有文章、數據、圖片均來自互聯網,一切版權均歸源網站或源作者所有。
如果侵犯了你的權益請來信告知我們刪除。郵箱:business@qudong.com